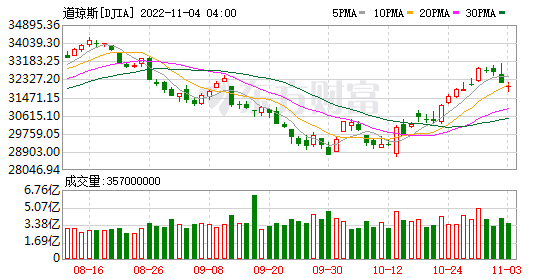上海,一座以繁华、丰富、海纳百川闻名的城市,拥有不计其数的时空细节。《消逝与眷恋》新书分享会于8月20日在上生新所·茑屋书店举办,邀请“上海相册”项目参展艺术家马良、摄影师席子和作家指间沙,分享存在于镜头、文字和其他媒介中的“上海时间”。

新书《消逝与眷恋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。
《彼岸花》:死去的时间,鲜活的时间
《彼岸花》是艺术家马良在这本新书中的作品。色彩暗淡的繁花与黑白的老照片组合成祭坛的形式,这种模拟的祭祀象征着对生命的祭奠。马良谈到他与这些照片的结缘,一位收藏老照片的同好请他帮忙辨认一批照片,其中包含相当多的上海细节。提及“老照片”,人们大多会想到照相馆,但马良指出这些照片出自一位掌握照相技术的男性——他是家中的男主人,拍摄的多为家庭照片,包括他的太太,还有孩子们的生活。
年代亦藏于细节。在一张照片上,一个女孩站在一口大钟上,高举手臂,摆出自由女神像的姿势。作家指间沙分享了这口钟的历史:1865年在美国建造,1881年被运至上海,原本属于一个救火会的瞭望塔。1922年左右,救火会不再需要这口钟,它便被挪至中山公园,1958年后不知所踪。
复兴公园、中山公园……老照片里熟悉的风景将马良与当年的人们连接起来。过去,人们说摄影是记录真实、留下记忆的手段,但马良从这些老照片里看到了摄影有些令人失望的一面:留在照片里的人到底是谁,多年之后已经无法查证。一个个曾经鲜活的面庞,曾经有过自己的名字,但现在都已经失去了。反复考证照片中的细节带给马良伤感,照片留下的似乎只是一场虚妄。马良后来选择用扫描仪完成《彼岸花》,而不是通过照相机摄取完成创作。对他来说,那些老照片已经臻于完美,其中记录了鲜活的生命,还有曾经的岁月都无法取代,很难再用拍摄的方式面对它们。
马良家的花园里生长着彼岸花。一天早晨,他发现原本都是叶子的位置开出了烟火般的红花,没有叶子,只有花,传说这种花开在冥河两岸。老照片中有一张拍摄的是一个花丛中的女孩,马良认出那种花就是彼岸花,这给了他一种感动。自己与那些生命的距离,似乎正如此岸与彼岸——他把这些作品,命名为《彼岸花》。
指间沙写作的照片,正是《彼岸花》。她借一本护士学校毕业册里真实的细节,结合《彼岸花》里的女孩们,创作了《嘉年华》。这些曾经鲜活的人们或许已经身在彼岸世界,但毕业册里的留言光明依旧,青春的活力和城市过去的摩登风采仍然留存。
彼岸花,马良 作品
彼岸花,马良 作品
彼岸花,马良 作品
彼岸花,马良 作品
《上海静物》:器物的时间,人的时间
静物安静、普通,容易被忽略,但也承载着人们生活的痕迹。摄影师席子谈到《上海静物》的创作,想法之一是“希望再细小一点,把镜头拉得更近一点”。他拍摄了很多八仙桌或餐桌的场景,大多数场景的位置他至今都记得。有两张,一张拍摄于东长治路,一张在山西北路。现在房子还在,但里面的人搬走了,东西也没有了,这是城市在变化的一个细小提示。对席子来说,感触最深的是人居住的最核心、最近的空间的变化。
举办分享会的上生新所也是城市变化的一环。席子打印了一些上生新所过去的照片,有的荒凉,有的空旷。他提到的变化:“我们的城市、老建筑、生活的空间,其实是时刻在变化的。虽然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,但是变化非常快。”
日常生活,也是席子长期关注并投入精力和情感最深的命题。城市容纳了不同阶层的人们,而静态的空间体现不同的人们对生活的要求。许多作品体现了这一点,比如老西门金家坊马路边上的一个水斗:洗漱、洗菜、洗碗,甚至冲凉,水斗代表着至少一部分上海人的生活场景。除了水斗,还有热水瓶。在没有热水器的年代,要用老虎灶泡开水,必须要有热水瓶。在《上海静物》的很多场景里,台子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热水瓶:竹壳的热水瓶,后面开始有塑料壳的,铁的,铝的,印着各式各样的图案。席子记忆,“早先在上海的普通人家中,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,如今基本消失了。”
为《上海静物》展开写作的作家陈心怡小姐评价这些照片,觉得“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生活的痕迹,像年轮一样全在里面了。”在席子长久、纵深的凝望中,《上海静物》浓缩了上海百年的时间,以及其中种种细小的生活痕迹。
上海静物,席子 作品
上海静物,席子 作品
上海静物,席子 作品
上海静物,席子 作品
时间魔法:破败的,美丽的,厚重的
上海一度被称为“魔都”。在这里,时间有自己的魔法。
马良经历过的“时间魔法”带着梦幻的色彩。90年代,动物保护意识尚不普及的时候,又加上他深受搞文艺的父母影响,他本着一种“座山雕”的“大王”想象,向马路上的一个回民购买了一张熊皮。这个回民成了他的朋友,后来一次交易,就在南市区的一个破旧的旅馆里。马良描述那个旅馆,用了“魔幻”一词:“我一去那个旅馆,很魔幻,玻璃顶的,地板是烂的,还有一点晃。整个建筑是非常美的老建筑,但是非常破败,破败到几乎要塌掉了,空中都是乱拉的电线。一个回民身上披了一块羊皮出来见我,我就开始跟他交易。”他后来查到这个地方,过去叫大东舞池,曾经是一个高级舞厅,有弹簧地板、玻璃顶。
马良的另一次梦幻经历是在一个教堂。同在夜校学习美术的同学邀请他去自己家,他们远远地看到一座教堂,同学说那是自己家。教堂里是一个棚户区,用破旧的木板搭出房屋。棚屋存在于一座教堂的古典结构里,头顶有破旧的壁画、损坏的彩色玻璃,还有鸟在建筑里飞。同学家的屋顶可以打开,马良就和他一起抽着烟,坐在床上往上看,场景不真实得如同一梦。城市的魔幻,在他后来创作的《邮差》《禁忌之书》作品中得以实现。
席子提到年轮。上海的空间曾经为他生动地演绎过这种意象。董家渡的一个弄堂里有一座房子,席子曾经记录下它从未拆到一点点拆掉的过程。房子搬空后的一天,席子进入其中,看到墙上贴着很多旧报纸,过去被居民们当墙纸用。他一层层剥开那些纸张,最里面的一层是房子建造时的老式墙纸,印花的。外面一层是二三十年代的报纸,印着明星、广告。再外面就开始有八十年代的《新民晚报》和其他报纸,贴了四五层乃至更多。墙上的报纸是一种意义上的年轮:在同一个生活空间里,上一任住户离开,新的住户进来,把原来住户的痕迹掩盖掉。从这些年轮里,席子窥见了时间,看见了整个时代。百年的历史和终将消逝的现实浓缩在一个画面里,堆叠出他希望记录的、上海城市空间的丰富变化。
城市的时间:变化的,静止的
在变化的时间里,老建筑成为一段时间内不变的地标。席子关注城市的变化,城市的飞速变化可能是一种幸运,也可能不尽如人意。一些老建筑可能会消失,也有一些被保留或重新利用,一如上生新所。他在B站上发布过上生新所的“前生”记录,对他来说,这些变化是值得记录的。另一方面,一些建筑不能完全满足住户的需求,但这并不是建筑本身的原因,历史、居住密度等因素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。许多建筑本身是应该被保留或重新利用的。
过去的城市记录多存于文字或摄影,但新媒介改变了这一切。更多人开始展示自己对城市的关注。席子回忆自己最早去拍武康大楼的经历,那时候淮海路、武康路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。某日,九点多,他跑到对面的兴国大楼顶上,拍下面的武康大楼。那一年下雪,冻得要命。
对马良来说,老建筑意味着城市生命的文脉。西方有一些著名的城市,一百多年的建筑在其中原封不动。他去荷兰,运河边上全部是歪掉的房子,几乎要倒了。当地人说这些建筑有几百年历史甚至更早,房子的主人没有拆,几代人几代人地留着。维修要花很多钱,比拆了花费的钱更多,但那条街道留下的是像伦勃朗时代一样的风景。“留下这个东西,这个民族才会有生命力。”马良说。
马良曾经写过一本书,谈作为上海小孩的成长史。他提到自己小时候读过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全部被拆掉了,大学也从原址搬离。过去玩的地方,溜冰的地方、舞厅都没了。“像我们这样一个号称上海人的人,其实没有坐标,只是会说上海话,”马良说,“作为一个上海人,我是没有根的,这其实很可怕。”
也有一些东西能够穿越历史。马良一直在收藏上海的老照片,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关于老照片的:他把收藏的老照片拿出来,重新感受其中生命的痕迹,并集结成书。
马良提到一座漂亮的汉白玉女神像,放在安福路一座洋房的花园里。“文革”时期,这座雕像本应被砸毁。当时的一群话剧艺术家,在一起开了一个会,最后大家决定把雕像头朝下埋在土里。1980年左右,“文革”余毒消除,少年马良看到人们用三角形支起的吊车,把雕像吊出扶正。那是一座维纳斯像,从土里挖出来被清洗,黄的一下变成雪白的。这尊雕像现在还在安福路的那个花园里,而走出花园来到网红街——安福路上,无数张青春脸庞从路的这一头走向另一头,人们像踏在T台红地毯上一般,呼啸而过,鲜少有人知道那尊雪白的汉白玉玉女神像曾经发黄过。
分享会现场席子(左)展示他打印出来的“上生新所”改造前的照片。
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婷在分享会前向读者介绍新书《消逝与眷恋》以及嘉宾。
在分享会的尾声,指间沙问到时间穿梭的问题。2011年,马良在微博上问过这个问题。2023年,席子的答案是回到上海的老城厢,去看水乡、桥和市井生活的场景。马良自己的答案很简单,回到2011年,那时几乎80%的答案都很动人。